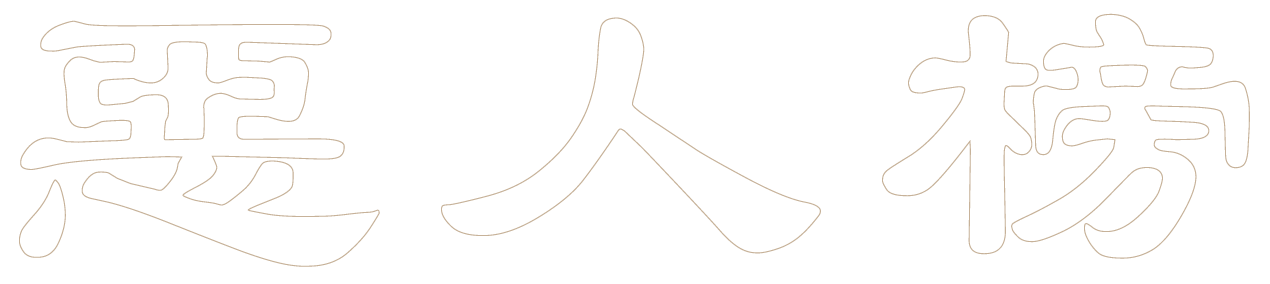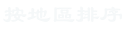劳教所电话:0531-88519942
四大队大队长:代秀峰还有张宏、李丽娟、韩建华、李春红、孔艳霞(音)、沈宏广(音)
各大队队长的名字
代秀峰、李利娟、李春红、孔宴霞、韩建华、张宏、张雪平、姜一帆、付晓莉、付?、沈洪广。
地址:济南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济南市浆水泉路20号)邮编:250014
电话:0531-8552194
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的部分恶警名单
所 长:姜丽杭 刘玉兰 杨某某
政治科:杨恩卫
宣传科:王信才
管理科:田薇 何绪芳
一大队:王淑贞 冯玉珍 孙秀凤
电 话:0531-8191744
二大队:许瑞菊 曹冬燕 殷传芳 徐红 李爱省 李敏 孙霞 王晓苇 刘芳 常某某
三大队:刘瑞芹 王月瑶 孙群丽 王云燕 许华 张洪芬 张亚雯 沈宏广 路莹 孔宴霞
电 话:0531-8191151 车间电话:0531-8555040-8035
五大队:牛学莲 梁巧玲 孙娟 李春红 孔庆华 张红 江某某 王某某 马某某 聂某某
以孙娟为首的省女所一大队的警察队伍的恶警:孙娟(大队长)、孙群丽(副大队长,主管所谓的学习、教育、洗脑转化)、耿筱梅(副大队长,分管奴役劳动)、杨晓琳(教导员)、李玉、梁巧玲、史咏梅、李妮(她们几个主要在车间管劳动),李敏、张洪芬、肖英、刘建慧(她们主要抓教育学习、洗脑与后勤管理等)。
孙娟、孙群丽、耿筱梅、杨晓琳为首的恶警造假有方,用她们自己的话说:自工作以来,我们就是对付法轮功,我们有的是“办法”。
杨晓林(教导员)、肖英,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警察为了“转化”大法弟子李秀娥,经常几天几夜不让她睡觉,让她蹲着。恶警张洪芬、耿小梅(三十多岁,老家德州)、杨小林指使邪悟的杨金凤(济南)、王海芝(临沂)、潘爱华(章丘)白天、晚上的看着她,不让睡觉。尤其在每个月写月小节时,都是遭受迫害严重之时。但迫害者表面很邪恶,实质很心虚,都是不敢见人的。晚上在晾衣房迫害,早晨起床时,把她转到队长的厕所里,白天在队长的值班休息室,不让睡觉,轮番来熬她,不让上厕所,不能上厕所,也无法吃饭、喝水,一直让蹲着,蹲的腿、脚都肿了。零七年六月底,蹲了四天四夜,后又蹲了五天五夜。她坚定说把恶警恶行曝光,恶大队长孙娟拽她头发,让她蹲着,让邪悟者打她,一直折磨了八、九天。
二零零六年,大法弟子詹丽华被非法关押在一大队期间,孙娟,杨晓林,孙群丽禁止她上厕所,逼她写背叛信仰的悔过书、 揭批书等所谓“三书”。
大法弟子韩爱雯绝食抗议被非法劳教以及非人的折磨,一大队大队长孙娟和孙群莉、杨晓林、李玉、李妮、耿筱梅、肖英和邪悟的包夹八、九个人一拥而上把韩爱雯摁倒在地上强行鼻饲。抽出鼻管的时候,鼻血脓块,半包卫生纸擦不完,惨不堪言。
二零零七年六月,刘京美给詹丽华传递经文,被包夹赵海霞(盗窃、二进宫)告发,恶警杨晓琳在班级会上大骂大法、大骂师父,并让全班,包括社会上普犯,人人表态,人人过关。韩爱雯听不下去,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正的。”一句话未说完,便被恶警杨晓琳早已安排好的普犯打手、包夹、连推带踢,挥手照脸便扇。中午吃饭时刘京美被留下,恶警杨晓琳威胁要关她禁闭。韩爱雯和詹丽华为了声援刘京美,两人不配合,不报数并绝食抗议。在餐厅,恶警肖英冲到韩爱雯桌旁,拍着桌子瞪着眼咬着牙说:“你不吃是吧,你是不想好了,把你关禁闭室,叫人帮助你吃,看你吃不吃。”说完气急败坏的拿起手机走到餐厅门口,啪啪啪的按,叫人来。结果,不知怎么搞的,事情莫名其妙的不了了之了。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恶警刘大伟带领几名警察,把程碧强行绑架到一辆警车上,送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零九个月。在劳教所,程碧被强迫照相、医院透视、抽血后,把她投进一大队遭迫害。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有孙娟、杨晓琳、孙群丽、耿狄(筱)梅、刘建会、梁巧玲、张洪芬、肖英、史咏梅、李玉、李敏、李昵等人。
为了达到让程碧放弃对法轮功信仰的目的,前三个月曾对她进行了隔离、封闭关押、挨冻、限制大小便、晚睡早起、不让洗刷、不让见亲人、长时间罚坐塑料板凳至臀部肌肉肿烂、强制洗脑等残酷迫害。接着逼迫她下车间劳动,几乎每天都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活,还经常强制早晚在宿舍干糊纸盒、贴标签等手工活。因高强度的奴役劳动,导致她每半个月来一次例假,每次持续半个月,而且流量很多,经常流到裤子里,有时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在床上打滚,有时在厕所呕吐,即使这样也不让休息。一次程碧痛晕在车间里,仅让休息两个小时,就又逼迫回车间劳动。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从起床、上厕所、洗刷、排队、走路、吃饭、喝水、干活、睡觉均不许说话,二十四小时被社会上的劳教人员监视,她们随时向恶警汇报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吃饭限制半个小时、洗刷五至七分钟、洗澡和洗衣服一共十至十五分钟,喝水限制次数,上厕所限制时间,经常大便没有解完就被赶出厕所,夜晚经常听到被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房间里传出来撕心裂肺的声音。在劳教所,程碧被迫害了一年零六个多月。二零零九年四月五日她回到了家。
二零一零年十月九日,恶警杨小林给苗培华戴上手铐,将她带到恶警医院作胸透心电图,检查结果为心脏病。苗培华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不配合打针做钡透,结果没有做成,还是被劳教所扣了200多元钱。10月110日晚,所长牛学莲来了,苗培华反映她被非法关进来时体重130多斤,现在却80多斤,这是被迫害的结果。结果第二天一早,恶警代秀峰带着王芳,刘建慧,李妮三个警察来了。她们把门窗关上,帘子挡上,用胶带封住她的嘴,宽胶带在头上连着缠了五、六圈。把苗培华五马分尸式的架起来。要强制拉苗培华去卫生所检查,并说让你告,我们有时间奉陪。并将缠在她头上的胶带硬撕下来,结果头发被撕下来很多。恶警们完全没有人性的大笑,连讽带刺的说风凉话。
恶警王芳把苗培华账卡偷走,代签她的名字,偷了400多元钱缴检查费。恶警杨小林故意派患有犹郁症的犯人看着苗培华。犯人发病时经常打她,掐她的脖子,撞她的头。清醒后又道歉说好话。说是恶警让她这样干的。
二零一零年春,杨晓琳开会回来,告诉包夹对法轮功学员要严、要狠,同时要对新抓来的法轮功学员加大洗脑力度。五月十三日清晨四点,翟金萍和同关一室的苗培华在监室的墙上挂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坐在床上打坐(她们一直睡地铺,快到出所时才让睡床)。恶警张洪芬有备而来,她换下了穿了几天的凉鞋,穿一双休闲皮鞋,过来两脚就把翟金萍踢下床。让帮忙的普教把翟金萍的上身用床单捆住,两腿伸平坐在地上。张洪芬坐在小凳子上,右脚踏在翟金萍的小腿上来回搓,只一次她腿上的皮肤都破了。翟金萍静下心来,集中精力看张洪芬的脚,张洪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赶紧拿下脚来。为了继续反迫害,翟金萍再次绝食。此时不善言辞,但耿直朴实的苗培华,早被带到监控看不到的房间挨打去了。张洪芬气急败坏,让人用抹布堵住苗培华的嘴,再用胶带粘住,用绳子捆住她盘起来的腿,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四点都没放开。后来张洪芬又一次打了苗培华,导致她发烧吐血。
有了上边加重迫害的指令,恶警们更加肆无忌惮。杨晓琳找了一个个头最高、胆子最大、姐夫是警察的普教李冰,背地里教唆她放手打人。又找来一根十八号的白色有方格花纹的平口硬质塑料管子给翟金萍灌食。由于管子太粗太硬插不进去,而且插的时候也有危险,她们就选了医务室负责人毕某来插(此人中专护士,不具备行医资格,因为给所长牛学莲当打手而当了负责人。她自己都说她给病人用了药,得等大夫来后再补处方)。她粗暴慌乱的把管子插进去,翟金萍就觉得一侧的额头、脸、脖子又热又痛、舌头都麻了。她一只眼睛往外流泪,流到脸上杀的皮肤很痛,半边额头、脸、脖子都烫手。杨晓琳为了让翟金萍痛苦难忍,吩咐拿好那专用的管子别用错了。插在翟金萍鼻子里的粗管子昼夜带着,不许拔,疼痛时时煎熬着她。一个值夜班的普教摸了摸她的脖子,顿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后来她被杨晓琳训斥,杨命令不许年龄大的普教和法轮功学员进翟金萍的房间,只许打人最狠、死心塌地帮她们“转化”别人的那个人进翟金萍的房间。三天后翟金萍觉的胃痛,她没吱声。又过了三天,她小便时,警察贾晶进来了,出于礼貌,翟金萍提起裤子,整理好衣服说:队长,我要上厕所。贾晶说:你就在这上吧。此后,翟金萍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被两个包夹连拍带叫的醒过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手握着双人床的一根钢管(不然就是躺着了),全身大汗淋漓,觉的想大便,就去墙角的马桶上方便,顿时很多血水倾泻而下。
这天晚上,贾晶早没了踪影(再一次见到贾晶已是二十天以后的事了)。当班恶警大队长代秀峰也没露面,身为警察在自己班上有人昏倒,她们不露面,已是法律上说的‘不作为’。就这样,翟金萍依然被罚坐到午夜以后才让休息。这天晚上,翟金萍解了八次大便,每次都是一股血水。第二天毕某来了,听包夹说翟金萍大便解了半桶黑血,又看了解手用的手纸上都是鲜血,就把翟金萍鼻子里的管子拔下来。下午杨晓琳来量了翟金萍的体温是三十七度八,就把她弄到武警医院检查(在入所查体后大约五十天左右,张洪芬还单独带翟金萍验了一次血,抽了大量的血),回来后,打了三天吊针,由劳教所夏医生给翟金萍换了一根十二号的软质淡黄色侧开口卵圆形正常胃管。每次灌食都有半汤匙白色药粉。有一次,恶警刘建惠值班,带着不满的口气问医生:怎么换管子了呢?医生瞪了她一眼,说她用十二号的,原来是十八号的。
二零一零年春,杨晓琳开会回来,告诉包夹对法轮功学员要严、要狠,同时要对新抓来的法轮功学员加大洗脑力度。五月十三日清晨四点,翟金萍和同关一室的苗培华在监室的墙上挂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坐在床上打坐(她们一直睡地铺,快到出所时才让睡床)。恶警张洪芬有备而来,她换下了穿了几天的凉鞋,穿一双休闲皮鞋,过来两脚就把翟金萍踢下床。让帮忙的普教把翟金萍的上身用床单捆住,两腿伸平坐在地上。张洪芬坐在小凳子上,右脚踏在翟金萍的小腿上来回搓,只一次她腿上的皮肤都破了。翟金萍静下心来,集中精力看张洪芬的脚,张洪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赶紧拿下脚来。为了继续反迫害,翟金萍再次绝食。此时不善言辞,但耿直朴实的苗培华,早被带到监控看不到的房间挨打去了。张洪芬气急败坏,让人用抹布堵住苗培华的嘴,再用胶带粘住,用绳子捆住她盘起来的腿,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四点都没放开。后来张洪芬又一次打了苗培华,导致她发烧吐血。
有了上边加重迫害的指令,恶警们更加肆无忌惮。杨晓琳找了一个个头最高、胆子最大、姐夫是警察的普教李冰,背地里教唆她放手打人。又找来一根十八号的白色有方格花纹的平口硬质塑料管子给翟金萍灌食。由于管子太粗太硬插不进去,而且插的时候也有危险,她们就选了医务室负责人毕某来插(此人中专护士,不具备行医资格,因为给所长牛学莲当打手而当了负责人。她自己都说她给病人用了药,得等大夫来后再补处方)。她粗暴慌乱的把管子插进去,翟金萍就觉得一侧的额头、脸、脖子又热又痛、舌头都麻了。她一只眼睛往外流泪,流到脸上杀的皮肤很痛,半边额头、脸、脖子都烫手。杨晓琳为了让翟金萍痛苦难忍,吩咐拿好那专用的管子别用错了。插在翟金萍鼻子里的粗管子昼夜带着,不许拔,疼痛时时煎熬着她。一个值夜班的普教摸了摸她的脖子,顿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后来她被杨晓琳训斥,杨命令不许年龄大的普教和法轮功学员进翟金萍的房间,只许打人最狠、死心塌地帮她们“转化”别人的那个人进翟金萍的房间。三天后翟金萍觉的胃痛,她没吱声。又过了三天,她小便时,警察贾晶进来了,出于礼貌,翟金萍提起裤子,整理好衣服说:队长,我要上厕所。贾晶说:你就在这上吧。此后,翟金萍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被两个包夹连拍带叫的醒过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手握着双人床的一根钢管(不然就是躺着了),全身大汗淋漓,觉的想大便,就去墙角的马桶上方便,顿时很多血水倾泻而下。
这天晚上,贾晶早没了踪影(再一次见到贾晶已是二十天以后的事了)。当班恶警大队长代秀峰也没露面,身为警察在自己班上有人昏倒,她们不露面,已是法律上说的‘不作为’。就这样,翟金萍依然被罚坐到午夜以后才让休息。这天晚上,翟金萍解了八次大便,每次都是一股血水。第二天毕某来了,听包夹说翟金萍大便解了半桶黑血,又看了解手用的手纸上都是鲜血,就把翟金萍鼻子里的管子拔下来。下午杨晓琳来量了翟金萍的体温是三十七度八,就把她弄到武警医院检查(在入所查体后大约五十天左右,张洪芬还单独带翟金萍验了一次血,抽了大量的血),回来后,打了三天吊针,由劳教所夏医生给翟金萍换了一根十二号的软质淡黄色侧开口卵圆形正常胃管。每次灌食都有半汤匙白色药粉。有一次,恶警刘建惠值班,带着不满的口气问医生:怎么换管子了呢?医生瞪了她一眼,说她用十二号的,原来是十八号的。
山东泰安优秀女医生两次遭劳教九死一生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1/17/山东泰安优秀女医生两次遭劳教九死一生-285662p.html
山东德州法轮功学员遭迫害部份案例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0/15/山东德州法轮功学员遭迫害部份案例-264064.html
原山东省府门诊部针灸师苗培华遭迫害经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5/30/原山东省府门诊部针灸师苗培华遭迫害经历-241681.html
河南周口淮阳法轮功学员李绍英被绑架勒索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21/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1年3月21日发表)-237850.html
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的罪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8/12/30/192536.html
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孙娟等恶警的恶行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8/10/30/188857.html
山东女子第一劳教所恶警及犹大暴行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8/8/21/184486.html#08820222654-3
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肖英恶行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8/7/28/182948.html#08727233715-4
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恶警耿筱梅的恶行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8/3/25/175093.html
揭露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幕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8/3/24/174931.html
曝光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孙娟等的恶行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8/3/23/1749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