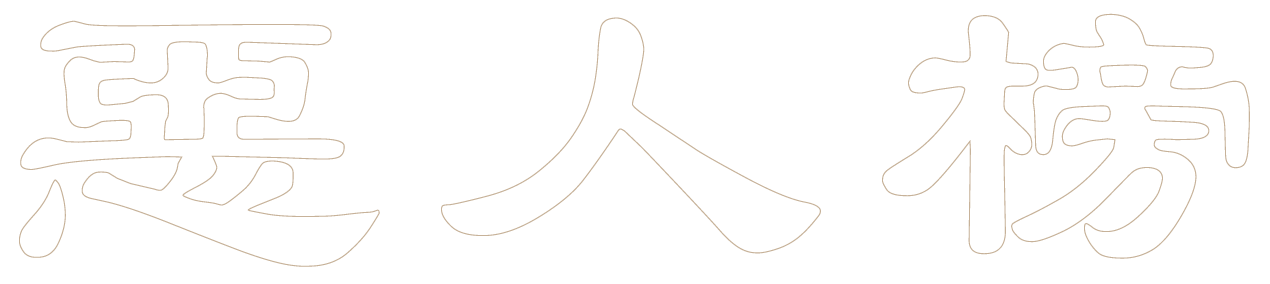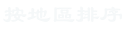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南口街34-2-5-1
大连市南林街175号 邮编:116001
总机:0411─6653961 办公室:0411-6641372
区号: 0411

在大连教养院,恶警隋子强、雍鸣久、(大)王军、(小)王军、林毅、孙有发等等,都是毒打大法弟子的凶手。
2001年1月9日,大法弟子坚持炼功,九个男警把她们集中起来,挨个问个还炼不炼,炼就打耳光。然后就拖出去打,把棉衣扒了用电棍电,打她的男警姓曲,电她的男警姓王,当时来的有大王军、小王军、林义、还有王某,是司机,还有雍其勇、孙永发(从大连戒毒所转来的)、还有一个副大队长,共十人,用皮鞋踢,拿拖鞋打十个法轮功学员,晕了就用冷水浇,打的满身是血,鼻青眼肿,臀部的颜色都是紫的,墙上都是血。
2001年1月12日,它们从早上7点半开始打满春莱,直到中午近12点。她醒来的时候是躺在地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昏的。在这之前是恶警大王军、小王军一起打,小王军打了一会走了,换林义(音),还有姓随的,随手里一直拿一根大伏特的电棍,不停的往手上的铐子上、脸上头上电,脸和头都被电烧破了;大王军和林义每人手里拿着一根警棒,从腰往下一人一个部位,棒子、电棍像雨点一样落在臀部、腿上、手上、脸上、头上,它们三个人累得把外衣全脱了,每人只穿件羊毛衫。又打了一会,把她用铐子吊在铁栏杆上,说不老实就这样,不知打了多长时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只觉得浑身动不了,最痛的是手腕子,因吊时手铐太紧,把手脖子上的肉给夹掉了一块,至今还落下一个疤。
2001年3月19日,大连教养院进行大规模强制“转化”,院长郝文帅等全院干警几乎全部出动。郝文帅亲自手持电棍往女学员的脸上、身上电击。致使很多学员的手、脸全是水泡。小王军、大王军、蒋仪(女)等人把大法学员按倒在地,有的骑在学员身上,有的按住学员的头,有的用电棍打、电击大法学员。恶徒们为了强制一位姓苗的学员放弃修炼,对她的迫害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
2001年3月至8月间在大连教养院,恶警乔威、王军等为了往上爬,而在长达4、5个月的时间里,对108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残酷施暴,昼夜不停地使用酷刑、殴打、虐待折磨。乔、王二人对单个的炼功学员,它二人也施以几个小时以上乃至整日整夜的4-8根高压电棍电击,胶皮棒殴打,老虎凳吊铐电击加殴打,头低向地面,手举向天的“小燕飞机”,经常性地对单人用4-8根电棍电击20分钟至半个小时。它们对百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肉体与精神上的极度摧残,除了“往死里打”的暴力之外,对近百名学员也极尽虐待、恐吓与折磨,不准睡觉,长时间背手挺腰坐马札子不准动,不准大小便,超体力劳动,不准说话,坐“飞机”。
恶警乔威、王军二人是因为“3.19事件”而被司法局处分调离的。后来大连610办公室在该市黑石礁XX宾馆办了一个专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禁闭、隔离、强行洗脑的所谓“学习班”,使用了臭名昭著的恶警乔威、王军。
从三﹒一九中午到晚上(2001年3月19日),从晚上又到第二天日出,被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的惨叫声几乎就没有停过。
在“三﹒一九”这个漫长的夜晚,恶警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谁睡就上电棍。
在仓库里,法轮功学员张军头缠纱布正躺在床上,手被铐着;曲辉脊柱被打断,躺在地上;王智勇被打得昏死过去,不省人事;高峰,张福明,殷延军、柳宗姚,张锡明,郑巍、滕志周,李吉胜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被手铐连手铐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大圏。这里的每个法轮功学员因不妥协都惨遭毒打,遍体鳞伤。
曲辉当时颈椎已被打断,已经瘫痪,不能动弹,非常痛苦,躺在地上呻吟,他一直是一个姿势躺着,椎骨断了非常痛,不停的说“给我翻翻身,给我翻翻身。”但恶警根本不予理睬,还不许他睡觉,不时的用电棍在他的脚上电一下,让他醒着。恶警诬陷曲辉,说是他上厕所时自残所致。曲辉说:我再有几天就到期出去了,我怎么会撞墙呢?
王智勇已经失去知觉,电棍过他脚时已经没有反应了,恶警摸他的脉搏时,已经感觉不到跳动。直到三月二十日的早晨天刚亮时,恶警电击他脚时,他才有感觉。
当夜在四楼监控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有:恶警小王军,孙健,雍鸣久,恶犯于世伟等,他们一晚上不断地用电棍电击学员,喝道“坐直”,法轮功学员们连坐的劲都没有了,恶犯们不断地用脚踹高峰的腰,一晚上踹了几十脚,用电棍电过高峰的脖子、耳朵和身上。
恶警小王军用几张大白纸写上大法师父的名字,逼迫学员坐在身下,并做了两三个侮辱大法的大牌子,挂在几个学员的脖子上。并强迫学员喊污蔑大法的三句话。
恶警小王军做了四个一寸宽,长二十厘米,高十厘米的严管凳,让人坐坐不下,蹲蹲不下,非常难受。
法轮功学员刘洪有后来从五大队小号被送到八大队严管班,就被强迫坐在严管凳上,因为刘洪有在五大队的小号中患上了疥疮,两天下来,白色的严管凳就被流出的脓水染黄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3/28/发生在大连教养院的“三一九”暴行-289228.html
大连教养院二零零一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纪实(3)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31/大连教养院二零零一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纪实-3--260734.html
大连教养院二零零一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纪实(2)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29/大连教养院二零零一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纪实(2)-260733.html
曝光大连监狱监狱长郝文帅恶行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1/曝光大连监狱监狱长郝文帅恶行-259627.html
五次非法关押 六年半残酷折磨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1/1/26/五次非法关押-六年半残酷折磨-235317.html
大连教养院恶警禽兽暴行:阴道里塞满辣椒面、满口的牙全被撬活动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1/4/88283.html
大连教养院恶警兽行:逼喝粪水 木条捅阴部 沸水烫脚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4/8/71900.html
大连教养院恶行曝光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4/60002.html
大连610洗脑班野蛮迫害大法弟子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0/27/59580.html
揭开大连电视台新视点节目为大连教养院精心打造的画皮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8/3/550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