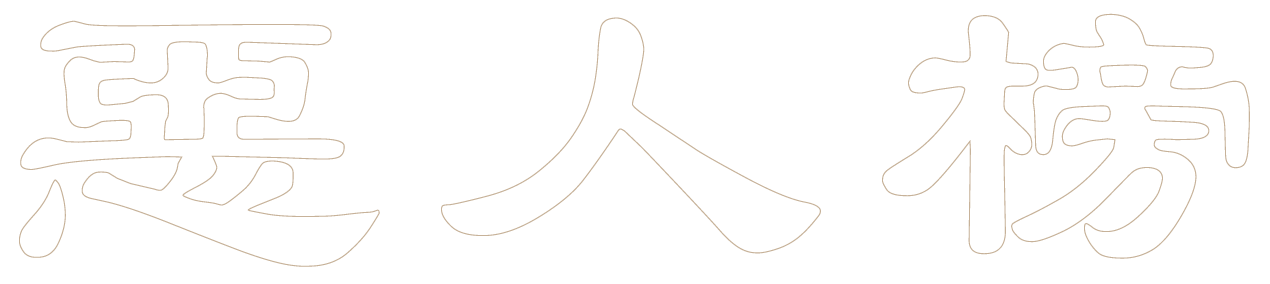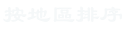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一大队0471-33392682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午,吸毒劳教人员夏聪玲被路俊卿从车间调上来接替原来监控贵州法轮功学员涂晓敏的李琴。夏被一队的人暗中称为“打手”,她身高1.68米,体重约八十公斤,因吸毒第二次被劳教,狱警们总利用她心狠手辣,争表现求减期的心理迫害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她暴打过的法轮功学员很多,就在她进库房的前一晚她还在库房暴打了法轮功学员李翠祥,当她被路俊卿从车间调出时,车间的人都说:“看,打手上去了”。
夏一来库房就凶狠地叫涂晓敏站起,她说:“你也是劳教人员,你没有权利,你去把队长叫来”。她冷笑说:“队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一边说着就伸手过来一把抓住她头顶的头发想把坐着的我提起来,一瞬间她的大部份体重被系于纤细的发丝,疼痛难忍,她想扳开她的手,她叫李琴把她的双手抓住,夏接着对她拳打脚踢,并用她粗壮的胳膊扣住她的脖子,使她几乎无法呼吸,后来俩人协同将她打倒在地,她的眼镜也被打变形,手脸被抓破出血,夏说:“你转化了我不敢动你,你不转化,我就敢打你。”她质问夏:“是谁给你的权力?”夏说:“是国家给的。”她高喊:“打人了!”夏却得意洋洋地说:“你喊吧,这楼上没人,没人听见。”她们她无所顾忌,非常嚣张。
后来吸毒劳教人员池艳霞也来助阵当帮凶,涂晓敏被她们打倒在地起不来,在冰凉的地板上躺着,当时正值她的例假期,她几次要上厕所,一想起身,就被她们按倒在地,不让起来,晚饭她们也没为我打,无吃无喝,又冷又饿,夏和池却谈笑风生。
车间的人收工回来洗漱后都睡下了,夜越来越深,她再次挣扎着起来要上厕所,池开门看了看,确信没有人看见她,才带她上了厕所。其实她们是怕人看见她的伤。
从厕所回来,她见值班室路俊卿在里面坐着,值班室的门和库房的门相对,她就站在外面说:“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睡觉?”池艳霞立即拽着她的头发慌忙往库房拖,夏聪玲本来睡下立即跳下床向她扑来,她们把涂晓敏拖进库房立即关上门对她施暴,夏用手拐猛击她的前胸,我高喊:“打人了”,但是路俊卿没有进来制止。在走廊值班的劳教人员(人们称为小哨)于双枝听到喊声,过来喊道:“打死她,把她吊起来”等。为了阻止她喊叫,夏找来擦鞋的脏毛巾要堵她的嘴。她合紧牙关,她们没有得逞,但她的嘴角、脸颊、嘴唇均被抓破,后来嘴唇肿了起来。
她被她们再次打倒在地,打累后她们就睡下了,她在冰凉的地板上躺到凌晨近三点,于双枝才让她放下床板铺床,因为全身多处受伤,当时她躺下和起身都很困难,借助库房放货的铁架才缓缓躺下。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凌晨五点,涂晓敏就被于双枝叫醒,不让她睡了,(全队劳教人员是到六点半才起床)她起床后,收了床板就靠站在窗台前,凳子被收走了。夏聪玲躺在床上睁眼看她,让她站好,她没理她,她就起床从地上捡了一只拖鞋来打她的手,打了左手打右手,要她放好手站军姿,她不从,她就又开始对她施暴,接着池艳霞也起来了,俩人一起施暴,她被打得眼冒金星,耳朵嗡鸣,她高喊:“打人啦,救命啦!” 这时于双枝也进来三人一起合力打她。因为全队还没有出工,她们听她喊就非常紧张,拚命来堵她的嘴,堵不上就用一大坐垫先盖住她的整个头,不让声音传出去。三个人合力将她按在地上,一只脚还踩在她的肚子上,夏聪玲拽着她的头死劲往地板上撞,她的头似要裂开一般,痛苦得无法形容。为了堵上她的嘴,她们好打的放心,她们又捏紧她的两个鼻孔,夏用手扼住她的咽喉,逼迫她张口,我几乎窒息,胸腔似要爆炸,她拚命摆动被压迫在地的头颅,藉着摆动中勒于嘴前毛巾的松动和唇齿间的缝隙透过的一点空气,才逃过生死一劫!
在被她们三人合力堵嘴的危急关头,路俊卿听到打闹声穿着睡衣来到了库房(当晚她值大夜班睡在劳教所),在那样危险的状况下,路不但没有阻止她们的暴行,而是大声喊道:“给我堵,堵住,拿大毛巾”。三人的恶行得到了队长的支持,更是有恃无恐,夏甚至说:“劳教所死个人算啥,所里每年都有死亡名额”。后来因为各班劳教人员都起床开始走动了,她们才收了手。
涂晓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不能动弹之际,路坐在夏聪玲的床边,开始冷言冷语对她训斥,训话间不时用穿着拖鞋的脚挑衅的触踢她的身体各处,她浑身疼痛头晕痛苦也无力说话,路训了一阵无趣才走了。
在她们二至三人多次对她暴力殴打的过程中,她自始至终没有作过任何的还击,在三人合力堵嘴使她窒息的时候,夏聪玲的手多次在她嘴边,她完全可以咬住她的手来解除不能呼吸的危险,可是在生死关头她依然遵循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的原则,她没有伤害她们任何人,可是路却颠倒黑白地说:“你是看我们内蒙人好欺负吗?”
这一天她又没有吃饭,因为限制上厕所,她几乎不喝水。到晚上一值夜班的王队长进库房查人数,她向她报告说:“她们打人”,队长对坐在地上的她瞟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谁打你了”,然后带上门走了。夏用无赖的口气说:“谁打你了,你自己碰的。”这正是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实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真实写照。她们对她身体造成的伤痛几个月后才慢慢恢复,很长时间她的耳鸣严重,还因右上牙及牙床受损,使一颗大牙后来掉了一半。
再见到路俊卿时,她严肃地正告她:“我差点被她们捂死,你以后要对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路为了开脱自己,只好当她的面对夏聪玲轻飘飘地说:“她是知识份子,以后你们不要动她。”后来她们就不轻易动手了,可见一切都是在队长的授意下干的。而且按路俊卿的说法,如果不是知识份子,遭受的就是更惨烈的摧残。
夏聪玲和李琴俩人二十四小时轮班监控她,对她看管很严,每次上厕所或洗漱都尽量让她避开其他人,特别不让她遇上别的法轮功学员。她一出库房门上厕所,队长或监控就要求在厕所或走廊的人全部回班,喊大家“回避”,如果途中偶遇别人,她向对方看一眼或微笑,夏聪玲就粗暴的怒斥她,让她回库房罚站,她只是不听她的,否则每天会被她们各种方式折磨。但是这些限制和处罚给人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在一个所谓的“文明”劳教所,她连微笑和张望一眼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在她们长期的施压下,她的头发开始一点点的白了。
她的作息时间和全队都不一样, 每天早五点起床,晚十一至十二点才能睡,中午不能休息。夏聪玲通常值夜班,她一睡下她就故意发出各种声响影响她入睡,有一天她很善意地提醒请她轻点声,她却更变本加厉。李琴嘲弄地说:“只有她敢叫你轻点声。”夏聪玲是真正的牢头狱霸,很多人对她敢怒不敢言,李琴也对她唯命是从,给她洗衣服送吃的,其实也都是看到夏得到路俊卿的重用,队里的规定夏都可以不遵守,比如按常规不能在库房洗漱,但夏每天打水回来洗几次,洗完满地的水让她擦干净,然后把洗脚水倒进她用来擦地打水的盆里,实质是让她给她倒洗脚水,就是这样的人每个月得到十天的最高减期,后来还进了民管会当卫生委员,而她却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被加期二十天。
因为不“转化”,除了每天让苑爱武等犹大来给她洗脑,或强迫她看洗脑用的光盘,洗脑用的教材,并要写出心得体会外,她们还变着花样折磨她。路要她每天用毛巾蹲在地上擦库房的地板和约八、九十米长的走廊。以前走廊都是用地布拖,现在要她用一小块毛布一块瓷砖一块瓷砖的擦,每块砖都要擦亮,没有痕迹水印,上午、下午劳教人员出工后各擦一遍,夏聪玲一看不如意就让她重擦,故意刁难。一天擦完库房擦走廊时因为蹲的时间太长,她的腿脚开始抽筋,这时她看见劳教所的所长孙锦琰在路俊卿的陪同下来一队查看,从走廊走过来,她吃力地站起来对她说:“孙所长,我从早上擦地擦到现在擦的腿抽筋”,夏聪玲不让她说下去,慌忙把她粗暴地推进库房关上门,对她威胁恫吓,过程中孙锦琰目睹一切没有作任何阻止和询问。该所一直标榜对劳教人员进行人性化管理,要用真情感化劳教人员,日前她还看到孙锦琰被评为什么“首届内蒙古职场女性榜样”,然而面对法轮功学员身心所受到的一切伤害,作为所长却是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这是什么榜样?可对外却标榜说:我们对劳教人员就像父母对孩子,像医生对病人!
二零零八年九月一天下午六点左右,张晓被恶警钟志荣扇了两巴掌。恶警又令吸毒人员挟持张晓到菜地施以暴力:包文君拿她掉下的鞋打她的头、脸、身上各处;李孬鸟、杨保原拿她被拽下的外套打;夏聪伶踢她的下身,这种摧残使她痛苦不堪。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0/8/27/228881.html
迷信中共的父亲可把女儿害惨了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0/2/23/2186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