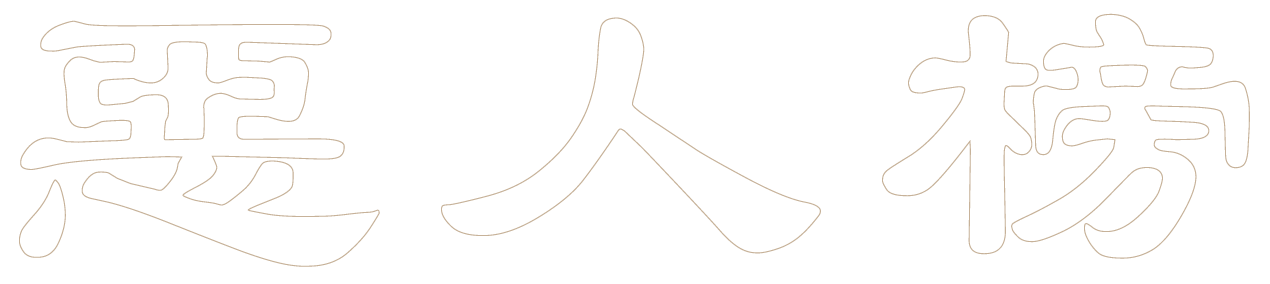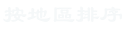总机:0451--84101454; 84101455 ;84101573; 84101509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史所长电话: 0451--4101454
七队电话: 0451--4103471,4103472,4103473
十二队电话: 0451--4103474,
总机:0451-86684001 转十三大队分机号:3473 ,3475
集训队十二队分机号:3476

哈尔滨市司法局劳教管理处
电话:0451-84610014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十六道街25号
邮编:150010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九日下午,队长赵余庆在大法弟子礼玉华血压高压190的情况下,亲自参与并指挥犯人白雪莲等二人给她上大挂,挂上多时,副队长姚福昌拿电棍多次反覆电她额头、上眼皮、耳垂、嘴唇、喉结处,在这之中,不断换电棍,不断增大电棍的电量。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依兰公安局将大法弟子孙锐非法劳教两年,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2001年1月31日在食堂背法,男队众多警察殴打女大法学员,孙锐因制止警察打人,被赵余庆等人揪着头发拽进七队小号长达三十八天。
二零零二年万家劳教所狱警赵余庆、姚福昌、张波、张艾辉、卢淑彬、刘涛、孙庆、刘文柱、张小初、姜家厚等对曾淑苓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迫害,刮疥疮,就是一个溃烂的小伤口,狱医孙立军用钢勺转圈一刮,就刮下一块肉来,变成一个大洞,鲜血直流,有的伤口都露骨头,再用过期的硫磺膏把大窟窿填平,造成她药物过敏,孙立军还说过敏就对了,她被酷刑迫害的几次昏倒,吸氧点滴抢救。
曾淑苓遭到的折磨还有:罚蹲、坐小板凳、上大挂、蹲小号、坐铁椅子、暴打、电棍电击,强迫写揭批侮辱谩骂师父,走正步军训、夏天阳光下暴晒、冬天扒光衣服冰冻等等,她还被迫长时间的劳动,编麻绳、缝汽车坐垫、做拖鞋、粘假眼毛;在万家劳教所两年的时间里她承受了太多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来,从十二队到七队及至集训队,恶警赵余庆与姚福昌等男恶警,按照上级安排进入女队已有两年多,违反了司法部“男干警不准管理女队员”的法规。
恶警赵余庆与姚福昌对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进所就逼写“三书” 不从者就上大挂、电棍击、坐铁椅、长时间罚蹲、拳打脚踢、不让睡觉喝水、 不让上厕所、不许家人接见、不许申诉上访、不许看法律书,长期播放诽谤数据、谩骂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背“誓词”、“守则”、“五不准”(为用于精神迫害胡编的东西当作法律法规来背)、反覆答题、反覆写三书、加期,凌辱人格、经济上乱收费、索贿受贿,等等。
恶警赵余庆将《大刀枪》的曲子编成诽谤大法,诽谤大法师父的歌,逼着法轮功学员唱,还搞出一个邪恶的诽谤大法的宣誓,逼着学员每晚必须背一遍。他用酷刑逼迫大法弟子说假话,骂大法及大法师父。在司法局的调查“转化”情况的问卷中,谁说真话他就体罚或上刑。
恶警赵余庆以给劳教人员办理提前解教为由,收取家人重金。例如:有的劳教二年,只呆了二三个月就走了。
于国荣在万家经常蹲地砖(体罚),不写三书就体罚,从早到晚蹲地砖,蹲的姿势不标准就连踢带打;整天坐小板凳,从早坐到晚,还用电棍电。在万家集训队期间,直接迫害人:队长吴国勋,副队长赵玉庆、姚福昌。
大法弟子王祝君因不放弃信仰,被罚坐铁椅子,犯人白雪莲代替写“三书”,王祝君把“三书”撕碎,恶警赵余庆罚她三百元。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七日,严码班劫持的全体大法弟子抵制邪恶,气坏了赵余庆。大法弟子周华,李文俊,王淑荣、孙丽芝等被拉出去上大挂(五马分尸)。余下的全部蹲在地上。恶警赵余庆还恶毒地搞所谓的宣誓。七队,十二队谁不附和就迫害,大法弟子于安然因不配合邪恶,多次遭到摧残,经常被罚蹲到十二点不许睡觉。
二零零二年五月,大法弟子宁淑贤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拘留两个多月,后被劳教三年,又劫持到万家劳教所。强迫写“三书”,宁淑贤不写,就开始罚蹲,从早晨五点一直蹲到半夜十二点。因宁淑贤股骨头坏死,蹲不了,浑身冒汗,心跳,浑身突突。科长赵余庆说宁淑贤有心脏病,让刑事犯白雪莲往宁淑贤嘴里塞速效救心丸。在集训队,姚福昌把改写的污蔑大法的歌作为队歌,每天早晚让法轮功学员唱。班长李宪梅、刘宏宇巡视,看谁不张嘴,就报告给狱警。李宪梅看宁淑贤没唱,于是报告给姚福昌,姚把宁淑贤和另一法轮功学员拉去罚蹲。等恶警赵余庆上班来后,他问宁淑贤为啥在这蹲着,姚向他说了原因,赵余庆就用小铐子把宁淑贤站着铐在床上,赵就开始打宁淑贤嘴巴子。打了一阵子后,赵、姚一人拿一根电棍,在宁淑贤的上半身到处电,把宁淑贤的脸都电黑了。
二零零二年三至七月,非典时期万家劳教所不让接见,恶警赵余庆却强迫大法学员屡次交钱。劳教所的大喇叭坏了,他与吴洪勋商定强行收取修炼人三百六十元做修理费,这笔钱不知流入了谁的腰包。强制戴的胸卡、糊窗户纸,逼每人交二元钱,谁要不交,就变着法儿的惩罚。赵余庆、姚福昌见有人公开抵制他们的经济迫害,就以出操动作不到位为由,把大法学员朱纯荣、郝沛杰等人拽出去在操场上惩罚。
恶警赵余庆利用普教犯人迫害大法弟子,许诺减大期、提前解教之机索贿,普教白雪莲、戴桂香劳教3年,只呆几个月或一半的时间便给减期,赵余庆在这方面受贿很多。
法轮功学员张春郁于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再次投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一次张春郁看经文,被徐凤平发现并举报,立即被十来个男女警察围住,将张春郁拽到女狱警宿舍(专门给法轮功学员用刑的房间),把她按在铁椅子上,双手反背过去后,再戴上铁铐子,两个凶相十足的男警察赵余庆和姚福昌一边站一个,手拿一根大电棍,同时往张春郁的脸上、嘴上、脖子上、手上,凡是露肉的地方上同时猛电,电棍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电棍所到之处,皮肉呈溃烂状,散发出烧焦的味儿。
每天警察赵余庆和姚福昌把所有的电棍充满电,叫人扒去张春郁外衣,只剩内衣,然后掀起内衣在后背排着电。这还不够,一次赵余庆抡圆了胳膊打张春郁嘴巴子,正打在她的左眼处,顿觉眼冒金花,眼珠要掉出来似的疼痛难忍,眼睛又青又肿了很长时间,现左眼已失明。张春郁的大腿被警察踢成红紫色,一片片,“大”字挂长达七天七夜。
二零零二年七月份,把法轮功学员张玉香送到了万家劳教所迫害。在集训队里,警察赵余庆和姚富昌把她锁在铁椅子上,手背在后边,手铐把双手腕扣住,把嘴粘上封条,一个狱警逼她写“三书”,她不写,说“真、善、忍”没有错。张玉香坐了五天五夜的铁椅子,腿都肿起来了,走路扶着东西或墙才能走,一瘸一拐的走,很多天才好。
警察赵余庆看张玉香不“转化”,就把她关到十二大队,每天逼坐小板凳,每天逼看诬蔑大法的录像、文章,不叫她睡觉,几个包夹每天围攻她,从肉体上、精神上折磨她。
二零零二年七月,魏亚云等大法弟子在万家劳教所集训队,遭受赵宇庆、姚福昌等狱警施用码板凳、电棍、大挂、蹲、不让睡觉等非人手段迫害。后来又把她们十几人关在一个屋子里,拉来几十箱筷子,让她们整天整夜的干活,不让睡觉,头发都熬白了。后来就用蹲、大挂、电棍等酷刑,放诽谤法轮功的电视迫害。不让睡觉,看诽谤电视,看邪党电视,困了就是连打再骂。
二零零二年七、八月左右,万家劳教所在七大队的三楼成立了以赵余庆、姚福昌(管理科)为首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训队。全大队各班级凡是坚持信仰的学员都被调到集训队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他们对学员的肉体迫害,轻者罚蹲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许说话,重者则单独拖到一个屋子里进行殴打、电棍电,有时警察将电棍插入学员的口中电、上大挂、五马分尸等酷刑折磨,整个集训队笼罩在阴森可怕之中,每天都有学员被酷刑折磨的惨叫声。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教师、法轮功学员郝沛杰曾被非法监禁在万家劳教所,遭受了残酷折磨,被女警察周木琴伙同刑事犯白雪莲等一帮人拳打脚踢,眼睛被打出血了,肋骨被打得疼痛难忍,动都动不了。二零零二年七月左右,郝沛杰在万家劳教所七队受迫害,由七大队长张波主谋,大所长卢振山决定,有四个男警察坐镇,郝沛杰被弄到七月二十五日在三楼成立的集训队,每天被强迫两手倒背蹲着,腿脚酸痛难忍,蹲到半夜只能睡二、三个小时,连蹲三天。开始不蹲,被白雪莲等四、五个由管理科科长赵余庆、姚福昌二人亲自挑选的女刑事犯打手打得眼睛充血,肋条打得不敢喘气,头发被薅掉了很多,打了很长时间才停止。
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他和恶警姚福昌对某刚入劳教所拒穿队服大法弟子打耳光,踢,踹,打得该大法弟子头昏眼花,头撞在暖气片上,在左眉上方留下深深的血迹,而且还罚蹲。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开始,万家劳教所的男干警进入女监,每班4个男干警,四个女干警,还有四个刑事犯全天监控看管大法弟子,每天要求大法弟子穿劳教服,戴胸卡,强迫背他们自编的诽谤法轮功的所谓“守则”,每天都必须“宣誓”,每周一次答卷,写“三书”。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他们所规定的上述要求说、写,他们就给大法弟子上各种刑具。给大法弟子上刑具的部门是所谓的管理科,三个科长叫吴洪勋、赵余庆、姚福昌。他们领着刑事犯毒打、迫害大法弟子,所用的刑罚有:电棍电击身体,长时间坐铁椅子、长期蹲小号、泼凉水、踢、打、长时间下蹲、双手倒背脚尖离地吊起。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号,劳教所派男狱警对女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迫害,有一次恶警因杨丽霞没戴牌遭毒打,还用电棍电脸部。还有一次,因不“转化”,恶警赵玉庆利用刑事犯给上大挂,双手被扣在门框子上,脚尖沾地,那手铐刹进肉里流着血,钻心地疼,疼得汗珠子像黄豆粒那么大。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起,十二大队、七大队,凡是恶人认为顽固的大法弟子都被绑架到集训队。在这里,人的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大法弟子们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严码班每天从早五点起床一直到半夜十二点都码在小塑料板凳上端坐,不许垫椅垫,不许闭眼睛,不许动弹,不许说一句话。
恶警赵余庆说:这回我再把你们变成哑吧。更残忍的是被劫持在这里的大法弟子二十四小时只能上两次厕所:早5点,晚九点各一次(弟子来例假也不许去厕所)。为了不让大法弟子夜间上厕所,赵余庆令人把便桶撤掉。除此之外还不许洗澡,不许洗衣服。一位大法弟子因在洗漱时洗了一件裤头被发现而受到迫害。
大法弟子何苗、高老师因不写“三书”被赵余庆剥去外衣铐在铁椅子上,全身浇上冷水放在七队二楼窗前,把窗子全部打开。当时正是深秋,夜间寒气逼人,两人昼夜不许回班。
崔淑香、何苗、高淑霞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跳楼抗议。崔淑香被抬走,赵余庆、刘涛、孙庆,张波等狱警冲进监舍,劈头盖脸就打高淑霞、何苗,陈贤君和仲晓燕去护两位同修,也被打到一边,打完又把高淑霞何苗绑到铁椅子上,往她们身上浇凉水,开窗户冻,迫害了好几天。还要迫害陈贤君,因铁椅子不够,恐吓要上大挂。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早晨,居委会主任敲门说是核实户口,吴雅琴去开门,闯进五,六个男的,他们说是道外国保大队警察,进屋到处乱翻,他们说要开「十六大会议」,让她跟他们到靖宇派出所谈话,结果把她送到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一个月,又把她送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万家劳教所集训队男狱警叫赵余庆,亲自动手,用拳头猛击吴雅琴的后脑,疼的差一点晕过去,又指使刑事犯人一起把她挂上大挂。赵余庆又指使犯人疯狂,残暴打她,用拳头砸脸,砸头,踢腹部,胳膊扭在后面吊挂着,疼的钻心刺骨,凶狠的往下砸胳膊,手铐像刀一样把手腕卡的皮开肉绽。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哈尔滨市某大法弟子拒绝写三书,被恶警赵余庆罚蹲。这样蹲到后半宿三点,上床躺了一个小时,次日五点又继续蹲。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左右,恶警赵余庆强迫全体法轮功学员写揭批,由于学员们不写违心话,两个大屋蹲点满了法轮功学员。赵余庆指使刑事犯白雪莲等狠命踢打代锐、六十四岁的刘秀茂、范春艳、郝佩杰、马丽达等7名学员,直打到他们站立不住。
二零零二年九月下旬,王莉又被转到三楼集训队,恶警赵余庆为了得奖金,不遗余力施用酷刑迫害大法学员,强迫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不然就酷刑迫害:上大挂、电棍电、用凉水往身上泼,每天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在当时许多大法弟子身上都长了脓包疥,他们就用带齿的勺刮。王莉的手腕上也长了一个脓包芥,他们就用带齿的勺刮,刮得血直往外窜,地上淌了一大片血,他们硬把王莉拽到卫生间,用凉水冲,有半个多小时血还是没有止住,他们说可能刮到血管了,就用纱布缠住血还是往外出,后来才止住。他们就这样残酷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
二零零二年十月杜秀琴被送到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集训队,集训队的恶警赵余庆、关杰还有姓张恶警等把她关一小屋,强迫她写‘三书’、出劳务、看电视洗脑、强迫被监规、遭包夹、出劳务、穿号服、出操。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因不放弃信仰又强迫礼玉华蹲了三天三夜,下午赵余庆把礼玉华带到一个单间,赵余庆从后边猛踢一脚,这一脚踢出她三米多远卡在凳子上。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一名女大法弟子被送到万家劳教所,因不配合邪恶,它们用各种酷刑折磨。赵余庆、姚福昌两个人一起把她吊着打,脸打肿了;用两根电棍一起电;五马分尸上大挂,挂两次;坐铁椅子三次。有一次上大挂,挂了一晚上。坐铁椅子坐了一个晚上。女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四月间,每天被迫蹲着,从早九点至十一点后,晚九点至十二点。一直遭受这种酷刑迫害长达四十多天。
劳教所长期逼迫大法学员强制洗脑,看反面电视。大法弟子们站出来不配合邪恶要求,吴姓科长、赵余庆对一女学员拳打脚踢,然后把她关在一个屋(不公开)坐铁椅,坐了十六个昼夜连一个白天。赵余庆和姚福昌用电棍电六、七次,每次都很长时间。有一次,女学员在铁椅上要上厕所,邪恶班长许凤平不让去,结果大小便都便在身上,棉裤都湿了,几天后才换下来,还不让洗脸。因她衣服穿的少,学员传递衣服给她,因这事科长姚福昌用电棍电击此学员,坐铁椅子,最后几天不让睡觉、不让合眼,二十四小时用刑事犯看着,合眼就骂,拿东西打脸;还坐着出水的铁椅子。
大法弟子唐秀丽就曾被劳教所科长赵余庆上过“大挂”。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七日,大法弟子吕慧文因答卷时讲了心里话,被赵余庆指使犯人王敏等把两手铐上,分别吊挂在左右两张两层高的单人床上,只有脚尖着地,这种刑罚叫五马分尸式的吊挂。
集训队成立迫害法轮功的小组,由刑事犯组成。这些犯人是管理科科长赵余庆、姚福昌二人亲自挑选的打手。大法弟子郝沛杰被他们迫害得最严重,上大挂时连踢带打,还用电棍。放下后十几个人一齐上,打得直翻滚,软肋骨挫伤,不能动弹,真是惨不忍睹,过后每天还强迫她出操。
二零零三年十月,法轮功学员杨悦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队长赵玉庆、科长姚福昌对她实施酷刑。
杨悦拒绝写“三书”,赵玉庆和姚福昌令她蹲在一个小瓷砖上反省。她不从。随后令四五个劳教人员一哄而上对她生拉硬拽,她拼命反抗,大声喊:“你们警察执法犯法!我不是没判死刑吗?等我出去,你们都得承担罪责!”赵玉庆慌忙用胶带纸将她的嘴缠了好几圈,边缠边骂。几个人强行将她按倒在铁椅子上。杨悦怒斥:“把胶带纸拿走!我鼻子不通气,死了算谁的?”赵玉庆忙又将胶带纸撕了下来。姚福昌凶神恶煞地扑上来,抡起电棍在她脸上、身上猛戳,边打边骂。她坚持不写三书,被铐在铁椅子上,不准睡觉,坐了五天五夜。五天没睡觉,身体忍受到极限,神志不清。直到她被迫签了字,才让离开铁椅子。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上旬,大法弟子于安然被严管迫害,十七天来不断的被恶警赵余庆电击,使双手、脸部溃烂。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石艳萍被送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强迫转化,因不遵守监规万家劳教所科长赵余庆将石艳萍双手绑吊在窗子上两脚不沾地用电棍电,还有一个吴洪勋科长两个人轮流电脸,脖子、耳朵后边,电的石艳萍两眼紧闭心发慌,电棍发出吱吱响声,耳朵肿大,铮亮,最后失禁他们才住手,这次石艳萍被他们酷刑折磨大约40分钟左右。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赵余庆把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两手铐到两层床床头上,拿来电棍在他的脸部、脖颈、手开始来回电,第二天早晨他的脸部、手部全部肿起来了同时上面都有均等的水泡,脸部都肿得变了形状。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下午,集训队由恶警赵余庆带领全队管教员考核,每名学员要单个宣誓、背守则,由于有十六名学员不愿说假话,而分别被上大挂,被电击,手段极其残忍。当时大法弟子李红梅,郝佩杰被十字挂于两床之间。
二零零四年五月,恶警赵余庆狠狠地打了李红梅两个耳光子。李红梅整整被折磨一下午。晚饭过后,五点开始在一块小地砖里边蹲着,不许出地砖的缝隙,一旦出缝犹大就用脚踢、踹,直到蹲到晚上十二点钟才让睡觉。连方便都不随便,只准早晚各一次。
恶人把大法弟子张秀琴从背后用手铐子把双手铐上绑在横梁上,整个身体悬空。恶警赵余庆一边用电棍电,一边问张秀琴谁,张秀琴说出她侄子的名字。又说出她大伯的名字。赵说这是我们前任处长。你爱人在哪上班?张秀琴说:“是省法院的法官。”
恶警赵余庆听了这些名字后停住了手,说:“你知道吗,这些名字救了你,要不我今天就把你毁了。”可张秀琴已被迫害得惨不忍睹:双手、脸、脖子水泡连成一片,双手的手腕被手铐扣到骨头,流着血。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大法弟子谭凤华被送到万家劳教所。在劳教所集训队里,谭凤华说:“法轮大法好!炼功病都好了。”管教周木齐就打谭凤华,这时科长赵于庆和两个帮教用手铐把谭凤华吊在铁门上,用电棍电。二零零四年六月中旬谭凤华的儿子给赵于庆二千元;同年七月末在哈尔滨请他们吃饭用去一千八百元。去依兰县巴兰河旅游,带队人赵于庆、吴红训、吴春霞一行八人;县去达连河避暑山庄,住宿一晚,第二天去丹青河报达山庄漂流,返回依兰吃饭,租两台车和买旅游用品共计一万三千元。旅游过程中又给赵于庆二千元。赵于庆谎言欺骗谭凤华儿子说:你妈抄经文又炼功犯罪了,她儿子又给赵于庆五千元,后来怕谭凤华受罪又给送去一千元。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日,大法弟子马桂云被用手铐吊了很长时间,胳膊都黑了,姚福昌、恶警赵余庆用新买来的电棍,电压很高,往她身上电,电一下就打一个跟头。
恶警们私自制定了三条谤法的话,被非法关押在此的大法弟子若不背就遭迫害。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大法弟子刘淑珍不肯背谤法的守则,被警察赵余庆拉到无人的房间进行迫害,因刘淑珍声明写的三书作废,他打刘淑珍耳光又用绳子把手捆住,拉着快走然后突然松开让刘淑珍重重的跌倒在地上,这样反覆折磨。
迫害时间待查,有一次恶警赵余庆把法轮功学员带到厕所,指使人扒光他们的衣服,发现经文、钱物等东西一律掠走。恶警赵余庆指使犯人白雪莲搜李玉华、马丽达等十五名法轮功学员的身,搜出约四百元钱。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三书”,不写,就强迫蹲在四十平方厘米的地板砖内,不准出格,手背到后面,不许动,动就拳打脚踢,从早上五点蹲到半夜十二点,几天下来,有的腿、脚被蹲得肿得不能走路,有的当场晕倒。这种酷刑叫“严码”。而且整天强迫看它们编制的污蔑法轮大法的影碟。每天二十四小时只准排两次便,如果还不写“三书”,就强迫坐“铁椅子”(一种酷刑刑具),并用电棍电,三、四个恶警一起电。
仍达不到目地,就给“上大挂”。还有更邪恶的酷刑:先暴打一顿,然后把法轮功学员锁在铁椅子上,鞋袜全脱,衣服脱到只剩裤头,从头顶浇凉水,然后拖到走廊窗口处打开窗户冷冻。哈尔滨冬天的夜晚零下三十多度,寒风刺骨,一坐就是几天几夜,冻得人浑身发抖,鼻涕直流,连六十五岁的老人也不放过,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活冻死、冻残、冻伤。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大法弟子张宏再次被非法劳教送到万家劳教所。不写三书,被上大挂。张宏开始绝食,二十六日恶警开始灌食,对了大量浓盐水。不让上厕所,白天上大挂,晚上坐铁椅子。后来因为她心脏不好,晚上让她睡光板床,手脚分别铐在床头床尾,不能动,屎尿都便在床上,恶警还故意把她放在风口处吹着,光着下身,上身只穿一件小背心,身上只给盖一个薄床单。二十九日灌食时,整条毛巾被鲜血染红(恶徒扔在厕所里被人发现),长时间站着脚肿成紫黑色。三十日给她打点滴前,集训队姚科长将点滴药瓶用凉水冲。
法轮功学员张宏,被狱警摧残的曾昏死过去。就这样,当时的女警李长杰,还跟队长赵余庆说张宏是装的。赵余庆说等张宏好一好再使劲的“收拾”她。
迫害期间她曾大声呼喊揭露恶警对她的迫害,被恶警指使劳教人员张桂云、陈玲玲、孙会君等用胶带将嘴封住(灌食等具体事都是这三个人实施)。三十一日下午四名男警察用担架将张宏抬走,走后对室内进行了消毒,据说送往211医院。恶警赵余庆后来掩盖说,张宏因心脏病引发肾衰竭而死。
八月五日为掩人耳目恶警将张宏呆过的的严管班“出所集训班”的牌子换成了“医务室”,并拿来氧气瓶等医疗用品布置室内。集训队的管教神色都很不自然,怕被人知道真象。张宏进来后一直呆在集训队(十三大队),主要恶警有四名男科长:赵玉庆、吴洪勋、姚福昌、栗小杰。张宏的家属现在正在上访,坚决不同意尸检及火化,要求走法律程序上告。
迫害时间待查,大法弟子李增云再次被劫持到万家劳教所的第一天,赵玉庆和恶警姚福昌及“犹大”徐凤萍等人还在一旁叫嚣着:强迫李增云写“三书”。由于李增云不配合邪恶,被罚蹲,又被上大挂,恶警姚福昌用电棍电她,她的脸全起大水泡了,然后继续被罚蹲,直到半夜十二点才让她睡觉,第二天四点多钟起床后继续被罚蹲。
二零零四年七月,平桂兰在小岭发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批劳教三年,在万家劳教所,从开始就屡遭迫害。经常被单独带到一个屋,锁在铁椅子,挨打、受酷刑。主要迫害人张波、张爱辉、赵玉庆、姚福昌、吴国勋等。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大法弟子刘淑珍被关进的当日,警察逼写“三书”,她不写。警察队长吴洪勋、副队长赵余庆把她双手铐在床梯上,罚在地上蹲着,这种刑罚蹲的一分一秒都很难承受。第八天早晨,在吴洪勋的授意下,副队长赵余庆又给刘淑珍上大挂,即用警绳把双手从后背吊到半空中,双脚离地。刘淑珍的腿因为七天六宿的蹲,神经已经蹲坏了,脚没有知觉,带不起拖鞋,站立不稳,姚福昌和吴宝云连打带踹的往刘淑珍的腿上踢,说她是装的。
二零零五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把刘淑珍叫到办公室,赵余庆对她说,明天领你去看病,你出去不能说,说了回来收拾你,还说检查出来病算我们的,我们掏钱。检查不出来病算你的,你掏钱。第一个大夫检查问,你的腿怎么整的,刘淑珍说不让说,大夫说你来时不是这样的,现在这样的,对吧。紧接着到下一个科,大夫说怎么整的,刘淑珍说蹲了七天六宿,警察李长杰说:“不说能瘪死你呀。”检查回来,赵余庆说没有病,意思是让刘淑珍负责检查费。但却带回来很多打针和吃的药,强行给她打针吃药。刘淑珍说没病吃什么药?没病还用吃药吗?!被他们就打,吃一顿打一顿,姚福昌打的多,拽着头发打,头发都一撮一撮的被拽下来。
二零零六年,因刘淑珍声明高压下写的“三书”作废,赵余庆打她三个耳光,又用绳子把手捆住,牵着快走,又用电棍电坏脚,然后突然松开,故意让她重重地跌倒在地上,这样反复折磨 。
二零零六年三月份,大法弟子苑桂华再次被非法劳教迫害一年,并被送到万家劳教所。万家劳教所大队长张波、恶警吴宏询、赵余庆等逼她在三楼上写三书,不写就给上大挂。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十三大队接见日,因为颜廷珍的家属在接见室将师父的法像取走,后被恶警要回,并停止接见三个月。主要责任人是刘涛和赵余庆。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黑龙江省十二名大法弟子被投入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集训队,四人当天被施以酷刑--坐铁椅子,其余八人因不写“三书”于十七日下午被吊打、电刑。直接参与者:吴洪勋、于芳莉、周木岐、韩顺善、赵余庆等。
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十二队。队长赵余庆非常阴险,姚福昌则是邪恶的打手。每天对大法弟子的围攻长达十七至十八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不让睡觉,不让走动,不让吃饭。强迫以固定姿势坐小板凳。小板凳是塑料的,坐时间长了臀部溃烂、化脓,烂到骨头,粘乎乎的沾到裤子上。
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被关进“小号”。冬天无被褥,大法弟子自身穿的绒衣被强行扒掉,再打开窗子,用冷冻迫害大法弟子。不让洗澡,不让上厕所(室内置一便桶)。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大法弟子曲凤英去同修家,刚到她家十几分钟,警察就利用一个人把门敲开,警察蜂拥而上绑架十几个同修,到公安局她们给他们讲真相,警察没打她,可是同修宁淑贤被恶警们严重殴打,并给她戴上脚镣子,审讯完又把她们送到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迫害关押三个多月,在此期间不让她们看书炼功,还让她们给他们干活,三个多月后把她劳教二年,送往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迫害。
刚到劳教所恶警赵余庆、姚福昌为了让她们“转化”(放弃信仰),体罚她们从早上5点一直蹲到半夜12点,期间有大法弟子都尿裤子里了,蹲不住恶警就连打带骂,还用电棍电她们,一直蹲了12天后,为了强行“转化”她们,赵余庆又给她们上大挂,同时姚福昌用电棍电她面部,强行逼迫她“转化”。她不妥协,他们就强迫她们在纸上签字。在劳教所期间他们还强迫她长时间奴役劳动,有些老年大法弟子完不成任务,他们就不让睡觉,还不让她们吃饱,每天受到恶警的谩骂、侮辱、殴打等迫害。快到释放日期,恶警们又以提前释放为诱饵让她在“转化书”上签字,被她严词拒绝。在一月十二日到期才被释放。
一次所谓的严管迫害中,大家被迫做奴工挑牙签,不许说话,五十多人的工作间里鸦雀无声。四个恶警科长手里拿着电棍,不时的把人叫出去用电棍电。十多天过去了,大家不停地发正念,那种精神上的恐怖压力几乎能把人窒息。一天刚吃过午饭回来,鲍丽云和身边一个同修交流,恶警赵玉庆把鲍丽云叫出去,抡圆胳膊打了鲍丽云四个耳光,并威胁鲍丽云不许讲出去,否则把鲍丽云弄进行刑室迫害。那次鲍丽云的上下牙床被恶警打得错了位,牙合不上,吃饭都困难,右上侧一颗大牙被打劈,里外分成两半,五天后里侧的一半褪了出来,牙神经裸露在外,其余牙齿变得疏松,三年后上下左右四个大牙全部坏掉。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张宏绝食抗议警察对自己的酷刑迫害。七月二十六日,队长赵余庆、科长姚福昌唆使其他警察对张宏强行灌食,警察在灌的玉米面粥里放入了大量的浓盐水。赵余庆、姚福昌下令不许任何人给水喝,不让她上厕所。长时间站着,她的脚肿成紫黑色。张宏身体被绑不能动,就大声的揭露坏人对她的迫害。警察就立即用胶带把张宏的嘴封住。七月二十九日,强行灌食后,整条毛巾被鲜血染红(警察扔在厕所里被人发现)。七月三十日,给张宏打点滴前,姚福昌将点滴药瓶用水冲的凉凉的然后再给张宏点滴。后来一天灌食三遍,每次灌食,警察和严管班班长张桂云等人就使劲拽张宏的头发,按脑袋强行插管,还污言秽语谩骂侮辱。
在极端的酷刑折磨中,张宏还在和这些迫害她的警察讲道理,好言相劝。而张宏却被他们摧残的曾昏死过去。就这样,女警李长杰还跟队长赵余庆说张宏是装的。赵余庆说等张宏好一好再使劲的收拾她。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多钟,无言的张宏被两个男警察和四个劳教人员用担架抬走,说是送往二一一医院(部队医院)。三点二十分家属接到通知,说张宏于当日下午两点心脏病猝死。后来队长赵余庆说张宏因心脏病引发肾衰竭而死。家属根本就没信那些警察的谎言,家人都知道张宏根本没有心脏病。
张宏走了以后,万家劳教所将张宏呆过的集训队严管班的牌子换成了「医务室」,并拿来氧气瓶等医疗用品布置室内。集训队的管教们神色都很不自然。当张宏的妈妈、姨妈、兄嫂等近十位亲人看到张宏遗体时,只见张宏双眼圆睁,嘴巴大张,口腔里全是血。裤内有大小便。身体明显消瘦,人比以前要瘦掉三、四十斤。家属问狱医心脏病猝死为甚么口腔里全是血(后两天没有灌食,而是打点滴),狱医说他解释不了。
家属看到张宏面目全非,要求给尸体录像和照像,被警察强行制止。他们催促家属尽快火化。家属不从,要求按法律程序进行尸检,却被劳教所的警察威胁恐吓。
张宏单位哈尔滨市第四医院给付的一千二百元丧葬费和家属的五百元钱一并被万家劳教所警察拿走。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9/8/15/迫害法轮功学员-各地警察、狱警遭恶报-391440.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7/6/4/两遭劳教受酷刑-哈尔滨吴雅琴控告元凶江泽民-349146.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7/2/23/三遭劳教-哈尔滨曾淑苓控告元凶江泽民-343442.html
修炼法轮功受益 哈尔滨刘淑珍遭劳教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12/6/修炼法轮功受益-哈尔滨刘淑珍遭劳教迫害-338582.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6/5/24/未婚妻被虐杀-哈尔滨孙玉峰控告恶首江泽民-329046.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0/17/二次被劳教-原黑
遭上大挂、坐铁椅 哈尔滨商人控告江泽民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0/3/遭上大挂、坐铁椅-哈尔滨商人控告江泽民-316893.html
龙江省电视台编辑控告江泽民-317676.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5/9/12/黑龙江五常市魏亚云自诉受迫害经历-315586.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5/6/9/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陈贤君遭受的迫害-310592.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5/15/张玉香自述遭酷刑经过-塑料鞋底殴打、针扎乳头-291933.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4/3/28/妇产科医生自述遭中共迫害经历-289257.html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3/12/9/哈尔滨市阿城区平桂珍三姐妹遭受的迫害-283750.html
黑龙江杜秀琴自述被迫害经历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3/2/4/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3年2月4日发表)-268473.html#1323234115-1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3/2/6/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鲍丽云自述遭迫害经历-269032p.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7/七年前,张宏被万家劳教所迫害致死-257645.html
黑龙江省依兰县法轮功学员石艳萍被迫害经历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2/2/23/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2年2月23日发表)-253312.html#12222224033-6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5/20/中共恶人的罪行-不会被岁月掩埋(图)-240377.html
杨丽霞遭冤狱八年 丈夫被迫害离世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1/5/232006.html
哈尔滨市王祝君、石秀云老人被迫害事实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0/1/230409.html
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苑桂华被迫害事实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8/18/228502.html
依兰县退休教师三次被非法劳教折磨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8/4/227939.html
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付桂芹自述遭迫害经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7/12/226824.html
黑龙江依兰县王莉自述遭受的迫害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0/2/8/217777.html
黑龙江依兰县曲凤英受迫害纪实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0/2/2/217317.html
黑龙江依兰县教师孙锐遭迫害纪实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10/1/13/216185.html
黑龙江依兰县礼玉华屡遭酷刑折磨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10/1/6/215784.html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及其它学校大法弟子遭迫害案例(图)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12/24/214996p.html
黑龙江省依兰县谭凤华遭受的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9/9/208011.html
于国荣在万家劳教所遭受的折磨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8/29/207364.html
揭露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对大法学员的迫害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9/4/23/199488.html#0942304413-9
万家劳教所迫害大法学员的酷刑种种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8/7/13/181950.html
我被万家劳教所迫害的经历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8/16/160945.html
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近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1/17/146997.html
黑龙江大法弟子李增云几年来遭受的迫害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6/9/22/138390.html
我在万家劳教所遭受的野蛮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7/12/132792.html
万家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行径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7/5/132207.html
警察扬言“不抓坏人,专抓法轮功”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6/21/130971.html
万家劳教所将刘淑珍迫害的不能自理,仍拒不放人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5/22/128462.html
黑龙江万家劳教所的虚伪和残酷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2/19/121180.html
万家劳教所的罪恶还在继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10/10/112086.html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部份犯罪记录(六)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5/8/7/107642.html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部份犯罪记录(一)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5/7/27/107022.html
阿城市李洪梅遭迫害五年 母亲哥哥被害死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7/16/106264.html
万家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5/8/101381.html
万家劳教所卢振山等恶警害死张宏的前后经过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2/16/95596.html
万家劳教所──邪恶的黑窝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5/2/10/95246.html
正告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恶警赵余庆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2/1/90428.html
揭露万家劳教所的罪恶(图)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13/89084.html
劳教所裂刑、吊挂、塑料袋窒息等酷刑演示(图)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0/30/87982.html
刚出狱大法弟子揭露万家劳教所暴行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10/22/87273.html
对害死大法弟子张宏的万家劳教所恶警的控告书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9/16/84324.html
哈尔滨市大法弟子张宏被万家劳教所迫害致死
http://www.minghui.ca/mh/articles/2004/8/16/81871.html
张宏被迫害致死 家属上访要求查明真像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8/19/82111.html
我被辗转关押后被劫持进万家劳教所遭迫害的经历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5/23/75172.html
万家劳教所血腥暴行录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17/65135.html
万家劳教所的酷刑和苦役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7/64254.html
黑龙江省依兰地区追查迫害法轮功者公告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4/1/4/64024.html
万家劳教所的罪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9/62120.html
万家劳教所酷刑:大挂、电棍、铁椅子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2/8/62072.html
万家劳教所恶警折磨大法弟子的各种野蛮手段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9/61479.html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成立所谓“集训队” 折磨大法弟子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5/20/50736.html
控告万家劳教所恶警酷刑逼供、故意伤害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23/48917.html
万恶之家”──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恶警暴行录(2002─2003年)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4/16/48499.html